
海洋科考船是探索海洋的一个重要工具,它像是一个流动的海上实验室,载着所有的领域的专家完成实验。与“科学一号”考察船相比,“科学”号有了动力定位系统,同时还搭载了无人缆控的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设备。“科学”号有哪些功能?科学家们又是如何安全回收设备、完整取回数据?
以下内容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科学”号首席科学家周慧演讲实录:
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有一句诗: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会和他有共同的感受,我们大家常常会把自己或喜或忧的情绪与大海联系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对大海有一种自然的喜爱。生命起源于大海,大海辽阔无边,似乎有包容一切的力量。
我们居住的地球有71%的面积由海洋覆盖。我国除了有960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面积,还有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所以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而且曾经也是一个海洋强国。
早在15世纪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就已经闻名于世了。我们曾经痛失过海洋,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换一种思维,正是这段屈辱的历史,让我们重新走向海洋。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制定了非常完备的海洋强国发展的策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海洋的资源开发、海洋的环境保护到海洋科技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我是1978年出生的,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在座的各位分享我所经历的中国海洋科技的发展历程。
我想大家很熟悉我国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它们是我国探索宇宙的重要工具。其实探索海洋与探索宇宙是很类似的,这两门学科都高度依赖人们的直接观测来获取认知。两门学科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上天,一个是下海。
谈到下海,海洋科考船是探索海洋的一个重要工具。大家可能会觉得与载人飞机、载人飞船相比,科考船更加接地气。因为在旅游的时候,大家可能乘坐过轮渡或者豪华游轮。
那么,科考船和我们乘坐的豪华游轮类似吗?是的。从外形上看,它们都是轮船,看上去差不多,但科考船的内部与游轮是完全不同的。
科考船上没有很美的观景台,没有豪华的餐厅甚至游泳池,有的是先进的海洋装备,我们要用这些装备到海上去做实验。所以,更确切地说,海洋科考船像是一个流动的海上实验室。
另外,科考船对搭载的乘客也是有要求的。除了维护船舶正常运行的船员以外,其他的乘客就是所有的领域的专家,大家要搭乘科考船去完成各自的实验。
科考船里还需要有一位首席科学家,负责在千变万化的海洋环境中,确保大家能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各自的实验项目,同时获取高质量的宝贵数据。所以,负责海洋科考的首席科学家有点像科考队员中的船长,带领大家在海上做实验。
我国第一艘具有大洋航行能力的海洋科考船是“科学一号”考察船。它建造于1980年,是由军舰改造的,并不是一艘专门为海洋科考而建造的科考船。
“科学一号”考察船的船长大约是104米,宽是14米。它是由军舰改造的,所以它跑得还是很快的,最大航速能够达到19节,相当于35千米/时。这艘科考船在当时属于世界先进的科考船。
1985年,中美两国开展的热带西太平洋海-气相互作用合作研究调查(简称“西太平洋联合调查”),用的就是“科学一号”考察船。
中科院海洋所老一辈的海洋学家,比如我们的胡敦欣院士等,都参加过中美的联合调查航次,这些调查航次使用的都是“科学一号”考察船。
但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对于海洋科考作业来说,“科学一号”考察船在有些地方是不太方便的。最大的不便就没有动力定位系统。
什么叫动力定位系统?我们在做海洋科考的时候,有一项需求,就希望能够原位作业,也就是尽量在一个地点作业。与此同时,考察船则保持位置相对不变,这样所取得的样品、获取的数据都代表了这一个点的变化。
在陆地上,这种要求好像很容易实现。但是在海上,科考船不仅会受到风的影响,还有表面海流、海浪的共同作用,它想保持不动是不可能的。所以,科考船就需要以动制静。这就是动力定位的一个基本原则。
我感触最深的是2014年我第一次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当时乘坐的就是“科学一号”考察船。那时,这艘船已经服役35年,甲板看上去很破旧,我们要作业的区域属于黑潮区。
大家可能对“黑潮”这个名词感到很陌生。直观来想,黑潮是不是就是黑色的?没错,黑潮确实是黑色的。又一想,黑色的水是不是很脏?没错,在陆地上,黑色的水往往意味着它可能不太干净。但是在海洋里恰恰相反,黑色的水表明它太干净了,以至于水中不含任何颗粒物。
当阳光照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没有颗粒物的散射,光都被吸收了。所以我们从海面上看,海水不是湛蓝的,而是黑蓝的,有时候从其正上方看,海水就是黑色的,这就是黑潮。
我们为何需要调查黑潮?因为黑潮对我们有重大意义。举例来说,日本有全球最大的北海道渔场,这个渔场就是黑潮对日本的最大馈赠了。
我们要在黑潮区开展作业,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平时在读文献的时候,我读到了很多关于黑潮的研究。在我心里,黑潮就像个老朋友一样,不过这个老朋友有些高冷,想和它亲密接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我们到达作业站点的时候,天公作美,天气还是可以的。我们下放了主要的观测设备温盐深仪(英文缩写为CTD),这个设备是用来观测海水温度、盐度和压力变化的,同时它还要采集海洋里不同深度的海水。这是我们的基础调查数据之一。
当观测设备放下去之后,刚开始还很顺利,缆绳可以竖直地往海底走。走到四五百米的时候,缆绳却往飘向船的外侧,往很远的地方漂过去了,也就是发生了“放风筝”情况。
这就是我们担心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因为缆绳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漂得太远,它的垂向就达不到实验预定的深度和观测需求。
我们正着急的时候,发现缆绳自己又慢慢地漂回来了。当时还觉得挺幸运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高兴,我们得知缆绳不光贴过来了,而且贴近了船舷的里面,直接钻到了船底。这时我非常紧张,我们最害怕的情况出现了,缆绳压船底了。
大家可能觉着压船底不是什么大事,把船底的缆绳拽出来就可以了。船底不就是一个斗型的平板吗?其实不是的。船在海里航行的时候,会有生物附着在船底。船底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贝壳,它们的外壳非常坚硬,缆绳被磨不了几下就会断,几百万元的设备可能因此就丢了,我们这个航次的科学考察也就失败了。
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我赶紧找了船长和工程技术部的负责人一起商量对策。尽管“科学一号”没有动力定位系统,好在船长还是很有经验的,凭着多年的操船经验,安全地把设备跟考察船分离开来。
事后,大家感慨说,如果用我们的新一代科考船“科学”号来作业,就不会发生这些状况了。
2016年,我第二次担任科考的首席科学家,乘坐的就是“科学”号考察船。与之前的“科学一号”考察船相比,“科学”号最优越的改进就是有了动力定位系统,考察船可以在规定的地点保持不变。
此外,“科学”号还搭载了新武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无人缆控的水下机器人。您如果有钱,也可以买一个水下机器人去海里抓宝,比如抓个宝石,或是找个古董。我们用水下机器人去抓的可能是以前从来就没见过的生物,甚至是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一种生命形式。
所以,无论是从作业的安全角度,还是配备设备的先进性,“科学”号比“科学一号”都有了革命性飞跃。
前面讲了很多与我们工作相关的“高大上”的东西,那么作为搭乘科考船的乘客,也就是科考队员来讲,先进的科考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想最大的感受就是淡水资源的改善。“科学”号配备了先进的海水淡化系统,科考队员在船上可以随便用淡水。但原来“科学一号”的淡水是有限供应的,一般是在起航后20天,就要限水了,大家不能随便洗澡,也不能随便洗衣服。
记得第一次乘坐“科学一号”出海的时候,船上的老师傅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年去热带做调查任务,当时船上慢慢的开始限水。有一天作业的时候,太阳非常晒,大家在温度高达70摄氏度的甲板上烤了半天,汗流浃背,想着如果能洗个澡就太舒服了,但是因为限水,没法洗澡。
这时候,天公作美,飘来一大朵乌云,甲板上下起倾盆大雨。大家高兴坏了,赶紧冲出去淋个痛快。船上有一个科考队员特别爱干净,他先去打了个肥皂,等他满身肥皂泡地跑到甲板上时,船已经开出了那朵乌云,雨停了。
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我笑得差点岔了气。但是,这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过的事情。
在“科学”号上,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在“科学”号上,每个房间都有淋浴装置,而且船上配备有海水淡化系统。大家在海上可以随便用淡水,随便洗澡。每次在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的甲板上汗流浃背地工作完以后,回房间冲一个温水澡,就能洗去一身疲惫。
大家也许会问,我们的祖国的研究人员为何需要跑这么远,到热带做观测?因为这里有全球面积最大、最暖的海水,我们叫它“暖池”。
如果把海洋环流系统比作人体的血液循环的话,暖池相当于我们的心脏。它的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给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国家带来天气灾害,甚至会极度影响我们的生活。
举个例子,如果暖池的温度上升0.01℃,那么它上方同样面积的空气温度要升高5℃。这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全球变暖,全球变暖会导致海平面上升。
此外,暖池也是厄尔尼诺的发源地。大家对厄尔尼诺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有所耳闻,比如,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主要是因为厄尔尼诺;2008年初,我国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也是源于厄尔尼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著名电影《后天》,影片中描述的就是海洋环流若发生异常,比如,热带的海水不再向高纬度流动,不再向寒带输送热量的话,我们的地球可能会重新再回到冰河世纪。
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科学家就开始在热带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海洋调查。当年我国科学家也参与了这些科考调查,为我们认识厄尔尼诺现象和相关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在这些发表出来的成果上,几乎看不到中国科学家的名字。这说明在那个年代,美国科学家并不是把中国科学家当成合作者来看待的,更多的是把我们的科学家当成打工的。这也表明,我们的祖国当时在这样的领域的国际地位是非常低的。
我的老师曾经非常感慨地说,我们没关于西太平洋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所从事的相关研究就像纸上谈兵。我们不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开着科考船,带着自己的科学猜想,到西太平洋去做实验。
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能轻松实现老师的理想。2010年,由我国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敦欣发起的“西北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实验”研究项目,经“气候变化与可预报性”国际组织批准,被纳入国际合作计划,成为一个大型的国际观测计划,吸引了来自8个国家、19个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参加。
这次的项目与之前我国研究人员参加的中美联合调查有根本性区别。这次是他们加入我们,来实现我们的科学猜想。
当然,任何科学猜想的成功都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它要求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这一点我本人有深切的体会。特别是对于海洋科考来说,海上环境变化莫测,不管你在家里做了多么完备的功课,到了海上,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一切努力可能都是白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6年的那次科学考察。当时,除了作为首席科学家之外,我还负责回收于2014年9月在西太平洋布放的3个压力逆式回声仪(PIES)设备。
这些设备的宝贵之处就在于监测了2015—2016年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中西太平洋的海洋环流数据。
出发之前,课题组组长袁东亮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一定要保证把这3个设施安全回收,并且要保证把数据完整地取回来。因为它们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当时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虽然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但到达作业站点的时候,因为压力比较大,加之海况也不是很好,前一天晚上,我其实并没有睡觉。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我们要在10月1日凌晨对设备做回收。压力逆式回声仪非常小,它是一个直径50厘米的球体,并且它在海上是白色面朝上,这使得我们很难在白天发现它们,只能在晚上进行回收。因为仪器上有氙气灯,在晚上会一闪一闪的,非常容易被发现。
凌晨0点,我们开始对回声仪来测试,以便确定其准确位置。当最终确定回声仪就在布放站点时,我在凌晨1:43按下了释放键。之后,便是漫长地等待。
按照回声仪的浮力计算,它大概需要90分钟才能漂到海面上。在这90分钟里,我和它是失联的,不知道仪器在上浮途中会发生啥。对我来说,这90分钟是非常煎熬的。
90分钟以后,大概在3:15的时候,我们紧盯着大海,丝毫不敢眨眼,就想着赶快出来一个闪光的亮点。但是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又盯着海面看了半个小时,一直等到天都亮了,我们仍旧是未曾发现闪光的球。
当时我的心沉到了谷底,人也有点蒙,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设备肯定是丢了。但是转念一想,既然设备丢了,那就应该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我先联系了国内的课题组组长,又跟原国家海洋局二所的朱小华团队的老师进行了沟通,他们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考虑到设备有无线电发射装置,我们大家可以利用无线电把它找回来。
但这样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没无线电接收装置,而且在海上也没地方能买到这些接收装置。
后来,我灵机一动,记起船上有很多无线电接收装置,于是就问船长船上有没有这一种评率的接收器。幸运的是,船长说船上刚好有3台这种甚高频接收器。我们就开始拿着接收器去找丢失的设备。
大家知道,无线电信号的有效距离只有几千米。从按下释放键到启动无线电寻找丢失设备,时间已逝去了七八个小时。按照当时的海水流速算,回声仪至少漂了十几千米。那么我们该到哪儿去找它?只有在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内,我们才有机会找到它。
冷静思考后,我想起搭载这个航次的研究人员中有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为“沈阳自动化所”)的金文明团队,他们携带有我国自主研发的水下滑翔机设备,该设备能在海面上对海流的流向和流速进行精确测定。
我与他们团队商量,请求其放下携带的水下滑翔机设备,帮我们测一下这一个地区的海流,以便确定该往哪个方向去找。金文明团队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之后,我们开着船,按照测定的流速去追丢失的设备。终于,在追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无线电有信号了。
但这时,我们面临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不知道回声仪在哪个方向。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无线电信号只有强弱之分而没有方向之别。为此,我请教了沈阳自动化所的研究团队,因为他们在仪器研发方面比较有经验。
他们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试着把无线电接收器的天线用锡纸屏蔽一下,并且在船上走动,看哪个方向在接收器被屏蔽后还有信号。如果屏蔽后还有信号,就代表了那个方向的无线电信号最强,回声仪就应该在同一个方向。
在上午11:40,我们用这个办法发现接收器出现了满格的信号。就在不远处,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白色的球,跳跃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中。那一刻,我至今难忘,这也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高兴的一刻,宛如重生。
后来,我们的同事说:“你竟然在这个直径50厘米的白球丢了10个小时,漂了十几千米后,还能把它找回来,绝对是人品爆发啊。”当时的我精神已经有点恍惚了,毕竟我有40个小时没睡觉了。
尽管如此,对于那片海洋,我依然心存感激。我觉着自己就像是大海的女儿,受到了大海的眷顾,让我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终实现了愿望。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时代,有国家给咱们提供的良好平台,让我们也可以在科技的海洋中自由驰骋。
有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美国一位知名的海洋学家,看见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研究成果,非常钦佩地说:“真羡慕你们能够在西太平洋做海洋科考!”
在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已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潜标观测网,能轻松实现对从深海到海底的海洋立体观测,而且实现了数据的实时传输。这一切都令我们为之骄傲。
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老渔夫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他说:“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渔夫和我们一样,都是海洋人,他的这句话完美诠释了海洋人的那种蓝色的情怀,也正是这种情怀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当晕船吐出绿色胆汁的时候,我还能坚持着把数据取回来。为了能到海上做实验,我可以把几岁大的孩子丢在家里,失联一个多月……
正是这种蓝色的情怀激励着我们海洋人,努力把我国从一个海洋大国建设成为真正的海洋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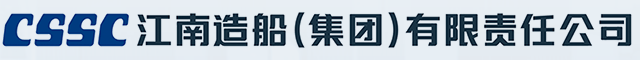

关注官方微信